徵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是台中南屯稅務諮詢會計服務推薦最佳稅務後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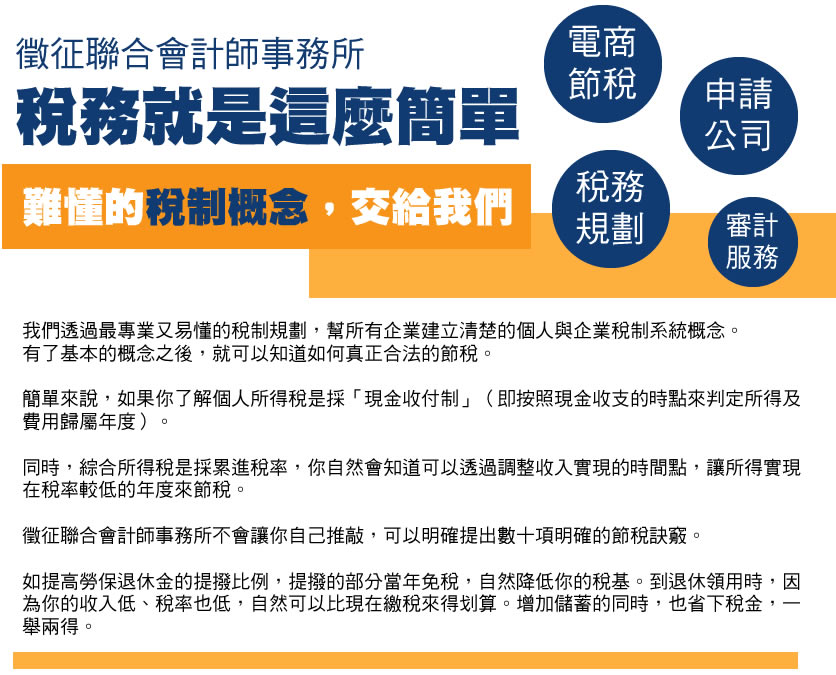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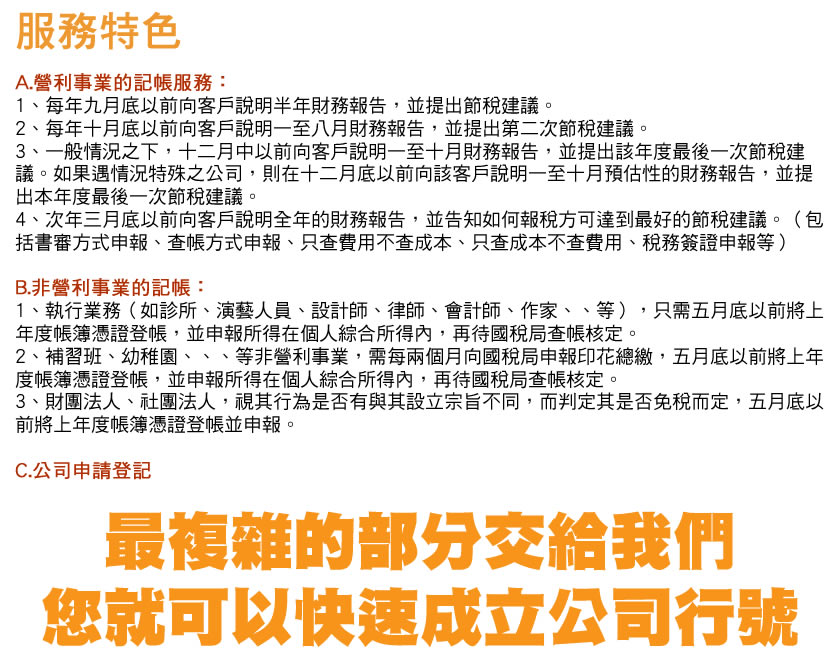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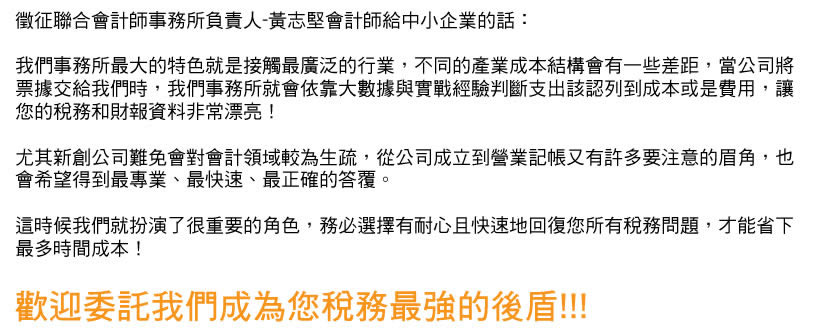
台中推薦公司投資及併購, 台中大雅風險諮詢會計服務推薦, 台中國際租稅諮詢會計服務推薦
別讓別人的看法,擋住了你的光芒 “別讓別人的看法,擋住了你的光芒”,這是最近火熱的菲律賓潘婷勵志廣告里的一句話,第一次看到這句話的時候,心里突突突直跳,我想起了最近的一個小事。 我有一個好朋友叫小C,她是一個做廣告的姑娘,同時是一個樂隊的吉他手,我畢業的第一年經常跟她混在一起,我覺得她就像陽光一樣,照耀著我那顆卑微的小心臟。每次她在舞台上表演,燈光打過來照在她身上的時候,我總覺得她的頭頂有一束光芒,伴隨著她的長發和搖擺的身姿,我覺得她這樣的畫面才叫青春,我簡直就是土到灰塵里去了。后來,我們彼此忙碌,漸漸聯系少了。看她的QQ空間感覺她后來回老家了,結婚生了一個孩子。前不久她來北京,我專門挑了一家賣樂器但還能喝咖啡的小店和她見面。 一見面,她先跟我抱怨了一個半小時婆媳矛盾,感嘆了物價的高昂與生活的不易,最后講述了她幫助女鄰居抓小三的故事。當我開始喝第四杯奶茶的時候,我問她:“你還談吉他嗎?”她一愣,很快反應過來,搖晃著她栗色的卷發大大咧咧的說:“早就不彈啦,我都有孩子了天天忙死了,估計早就忘了怎么彈了。”說這句話的時候,她的眼神突然落寞了下來。她跟我說,那些年白天上班,晚上唱歌,自己過的特high,但老板覺得她不務正業,盡管從未因為樂隊的事情耽誤工作,這種不信任感讓她特別難受;加上父母跟她說:“咱家祖上三代,方圓兩公里內沒出過一個玩音樂的,你是我們生養的,我們還不知道你?女孩子那么瘋干什么?趕緊回來找個對象才是正經事。”這句話,讓她心里蒙上一層麻袋,收拾東西真的回老家了。 我心里突然特別難受,難受的想要抱著她哭,我不也是那個一直一邊白天工作,一邊深夜寫字為自己的小愛好折騰不停的女孩么?這些年,一直被家人認為是忙著不找邊際的事情,一直被同事和領導認為上班時間工作量不足,才能下班還有力氣和精神去忙自己的事情。為了不被人說,曾暫停了大部分個人愛好沒日沒夜的加班的過后,依然會被打上各種奇怪的標簽。只要你不聽話,不像一個機器一樣乖乖做事,就永遠不會被身邊人肯定。可是,當我真的放棄自己想做的事情,變成別人目光里的乖乖的女孩兒的時候,我活得特別沒勁,生活里連值得興奮和開心的事兒都感覺不到了,曾經的光芒閃亮連自己都看不到了。可光芒這種東西,太刺眼,一定需要穿破點什么才能看得到的。 我太理解這種不被人信任的感覺,太明白這種無聲的厲喝的帶來的摧毀和打擊,以至于后來有家公司的總裁和顏悅色的跟我說“我只想讓你來我的公司,干什么都可以,我相信你”的時候,我居然嘶吼嘶吼的回家哭了一整夜。我一直相信,人是會不斷變化的,不光身體外貌,包括內心與品格;我也一直相信,自己也是不斷變化的,小時候怯懦忍讓,不代表長大后不會橫沖直撞。除非,自己放棄了自己,活在了別人一成不變的目光里。 這些年,我總是收到好多好多為自己的夢想不斷拼命抗爭的年輕人的來信,特別是女孩子,無論是社會的壓力,還是自身的不自信,總是會被別人的一句話打擊的掉下眼淚,放棄了自己喜歡的事情,甚至是曾經自己努力爭取來的一切。比如父母會下定論一般說“不用那么拼,找個男人是正事”,或者被同事和老板隨便貼個標簽便欺負折磨看不起,再或者被別人勸說女孩子養好孩子顧好家才是重點,女強人很容易找不到對象的哦!每次看到那些眼神靚麗的姑娘進入社會沒多久就會變成灰頭土臉的模樣,心里就特別不是滋味兒。可你問我該怎么打贏這場戰役,其實我不知道,因為我也一直在抗爭,在努力,在別別扭扭的保護著夢里的那棵樹。我在半夜里哭過,被某些人一句話壓的喘不過氣過,懷疑甚至差點放棄過。可總有那么一些時刻,一些人一些事一些音樂一些畫面提醒著你,親愛的,你已經走了這么遠,努力了那么久,千萬別縮回身,活成你曾經最看不起的樣子。 “趁你還不需要翻來覆去考慮又考慮/趁你還不知道為什么嘆氣/趁你還沒學會裝模作樣證明你自己/你想什么什么就是你……”上周五去看《等風來》,對電影的感覺一般般,卻被大媽們在酒吧里唱的這首《趁你還年輕》擊中,瞬間飆淚在電影院里悄悄流了一脖子淚。對于我們每個女孩子來講,如果你想抗爭,青春就是一場開戰了就再停不下來戰爭,唯一不同的是,這是一場重在參與的戰爭,無論勝負,無論輸贏,生命會在這場戰爭中留下風殘云卷的痕跡,或熱烈,或激昂,或慘烈,或悲愴,但不管結果如何,只要足夠勇敢,足夠堅定,足夠把自己當一個人來看,總會活出自己的光芒。別害怕,別回頭,別讓別人的看法,擋住了你的光芒,趁你還年輕。 那天下午的后來,我在樂器店里拿了一把吉他遞給小C,她扭搭了半天擺出一個Pose,撥拉撥拉琴弦,彈出了當年我們都熟悉的那些歌兒,越彈越high,越high越瘋狂。雖然她不再甩著掛面一樣直而細的長發,但我仿佛看到了,她那曾經照亮我自卑小心臟的光環,在那個午后的陽光里,又回到她的身旁。她肆意的大笑,她閃亮的眼神,她癲癇一樣搖擺的身軀,她凌亂的頭發卷,就像一顆樹,在風中凌亂但自由的飛舞著。 別讓故事只是故事 別讓抱怨毀了你的工作生活 沒有人在意你的青春,也別讓別人左右了你的青春分頁:123
茅盾:大鼻子的故事 在“大上海”的三百萬人口中,我們這里的主角算是“最低賤”的。 我們有時瞥見他偷偷地溜進了三層樓“新式衛生設備”的什么“坊”什么“村”的烏油大鐵門,爬在水泥的大垃圾箱旁邊,和野狗們一同,掏摸那水泥箱里的發霉的“寶貝”。他會和野狗搶一塊肉骨頭,搶到手時細看一下,覺得那粘滿了塵土的骨頭上實在一無可取,也只好丟還給本領比他高強的野狗。偶然他撿得一只爛蘋果或是半截老蘿卜,——那是野狗們嗅了一嗅掉頭不顧的,那他就要快活得連他的瘦黑指頭都有點發抖。他一邊吃,一邊就更加勇敢地擠在狗群中到那水泥箱里去掏摸,他也像狗們似的伏在地上,他那瘦黑的小臉兒竟會鉆進水泥箱下邊的小門里去。也許他會看見水泥箱里邊有什么發亮的東西,——約莫是一個舊酒瓶或是少爺小姐們弄壞了的玩具,那他就連肚子餓也暫時忘記,他伸長了小臂膊去抓著掏著,恨不得連身子都鉆進水泥箱去。可是,往往在這當兒,他的屁股上就吃了粗牛皮靴的重重的一腳:憑經驗,他知道這一腳是這“村”或“坊”的管門巡捕賞給他的。于是他只好和那些尾巴夾在屁股間的野狗們一同,悄悄逃出那烏油大鐵門,再到別地方進行他的“冒險”事業。 有時他的運氣來了,他居然能夠避過管門巡捕的眼睛,踅到三層樓“新式衛生設備”的一家的后門口,而又湊巧那家的后門開著,燒飯娘姨正在把隔夜的殘羹冷飯倒進“泔腳桶”去,那時他可要開口了;他的聲音是低弱到聽不明白的,——聽不明白也不要緊,反正那燒飯娘姨懂得他的要求,這時候,他或者得半碗酸粥,或者只得一個白眼,或者竟是一句同情的然而于他毫無益處的話語:“去,不能給你!泔腳是有人出錢包了去的!” 以上這些事,大概發生在每天清早,少爺小姐們還睡在香噴噴的被窩里的時候。 這以后,我們也許會在繁華的街角看見他跟在大肚子的紳士和水蛇腰長旗袍高跟鞋的太太們的背后,用發抖的聲音低喚著“老爺,太太,發好心呀”。 在橫跨蘇州河的水泥鋼骨的大洋橋腳下,也許我們又看見他忽然像一匹老鼠從人堆里鉆出來,躥到一輛正在上橋的黃包車旁邊,幫著車夫拉上橋去;他一邊拉,一邊向坐車的哀告:“老爺,(或是太太,……)發發好心!”這是他在用勞力換取食糧了,然而他得到的至多是一個銅子,或者簡直沒有。 他這樣的“出賣勞力”,也是一種“冒險生意”。巡捕見了,會用棍子教訓他。有時巡捕倒會“發好心”,裝作不見,可是在橋的兩端有和他同樣境遇然而年紀比他大,資格比他老的同業們,卻毫不通融,會罵他,打他,不許他有這樣“出賣勞力”的自由! 就是這樣的“冒險生意”也有人分了地盤在“包辦”,而且他們又各有后台老板,不是隨便可以自由營業的。 但是我們這位主角也有極得意的時候。 這,通常是在繁華的馬路上耀亮著紅綠的“霓虹燈”,而僻靜的小巷里卻只有巷口一盞路燈的冷光的時候。我們的主角,這時候,也許機緣湊巧,聯合了五六個乃至十來個和他年紀相仿的同志,守在這僻靜的小巷里。于是守著守著,巷口會發現了一副飯擔子,也是不過十二三歲的一個孩子挑著,是從什么小商店里回來的。這是一副吃過的飯擔子了,前面的竹籃里也許只有些還剩得薄薄一層油水的空碗空碟子,后面的紫銅飯桶里也許只有不夠一人滿足的冷飯,但是也許運氣好,碗里和碟里居然還有呷得起的油湯或是幾根骨頭幾片癩菜葉,桶里的冷飯居然還夠喂一條壯健的狗;那時候,因為優勢是在我們的主角和他的同志這邊,挑空飯擔的孩子照例是無抵抗的。我們的主角就此得了部分的滿足,舐過了油膩的碟子以后,呼嘯而去。 然而我們這位主角的“家常便飯”終究還是挨罵,挨棍子,挨皮靴;他的生活比野狗的還艱難些。 在“大上海”的三百萬人口中,像我們這里的主角那樣的孩子究竟有多少,我們是不知道的。 反過來說,在“大上海”的三百萬人口中,究竟有多少孩子睡在香噴噴的被窩而且他們的玩厭了弄壞了的玩具丟在垃圾箱里引得我們的主角爬進去掏摸,因此吃了管門巡捕的一腳的,我們也不大曉得。或者兩方面的數目差得不多罷,或者睡香噴噴的被窩的,數目少些,我們也暫且不管。 可是我們卻有憑有據的曉得:在“大上海”的三百萬人口當中,大概有三十萬到四十萬的跟我們的主角差不多年紀的孩子,在絲廠里,火柴廠里,電燈泡廠里,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工廠里,從早上六點鐘到下午六點鐘讓機器吮吸他們的血!是他們的血,說一句不算怎么過分的話,養活了睡香噴噴被窩的孩子們以及他們的爸爸媽媽的。 我們的主角也曾在電燈泡廠或別的什么廠的大門外看見那些工作得像人蠟似的孩子們慢慢地走出來。那時候,如果他的肚子正在咕咕地叫,他是羨慕他們的,他知道他們這一出來,至少有個“家”(即使是草棚)可歸,至少有大餅可咬,而且至少能夠在一個叫做屋頂的下面睡到明天清早五點鐘。 他當然想不到眼前他所羨慕的小朋友們過不了幾年就會被機器吮吸得再不適用,于是被吐了出來,擲在街頭,于是就連和野狗搶肉骨頭的本領也沒有,就連“拉黃牛”過橋的力氣也沒有,就連……不過,這方面的事,我們還是少說些罷,我們還是回到我們的主角身上。 他不是生下來就沒有“家”的。怎樣的一個“家”,他已經記不明白。他只模糊記得:那一年忽然上海打起仗來,“大鐵鳥”在半空里撒下無數的炸彈,有些落在高房子上,然而更多的卻落在他“家”所在的貧民窟,于是他就沒有“家”了。 同時他亦沒有爸爸和媽媽了。怎樣沒有了的,他也不知道;爸爸媽媽是怎樣個面目,現在他也記不清了,那時他只有七八歲光景,實在太小一點;而且爸爸媽媽在日,他也不曾看清過他們的面目。天還黑的時候他們就出去,天又黑了他們才回來,他們也是喂什么機器的。 不過,他有過爸爸媽媽,而且怎樣他變成沒有爸爸媽媽,而且是誰奪了他的爸爸媽媽去,他是永久不能忘記的。他又明白記得:沒有了爸爸媽媽以后,他夾在一大群的老婆子和孩子們中間被送進了一個地方,倒也有點薄粥或是發霉的大餅吃。約莫過了半年,忽然有一天一位體面先生叫他們一伙兒到一間屋子里去一個一個問,問到他的時候,他記得是這樣的: “你有家么?” 他搖頭。 “你有親戚么?” 他又搖頭。 于是那位體面先生也搖了搖頭。用一枝鉛筆在一張紙上畫一筆,就叫著另外一個號頭了。 這以后,不多幾天,他就糊里糊涂被擲在街頭了,他也糊里糊涂和別的同樣情形的孩子們做伴,有時大家很要好,有時也打架,他也和野狗做伴,也和野狗打架;這樣居然拖過了幾年,他也慣了,他莽莽漠漠只覺得像他這樣的人大概是總得這樣活過去的。 照上面所說,我們這里的主角的生活似乎頗不平凡然而又實在平凡得很。他天天有些“冒險”經歷,然而他這樣的“冒險”經歷連搜奇好異的“本埠新聞”版的外勤記者也覺得不夠新聞資格呢。 好罷,那么,我們總得從他的不平凡而又平凡的生活中挑出一件“奇遇”來開始。 何年何月何日弄不清楚,總之是一個不冷不熱沒有太陽也沒刮風也沒下雨的好日子。 這一天之所以配稱為他生活史上的“奇遇”,因為有這么一回事。 大約是午后兩點鐘光景,他蹲在一個“公共毛廁”的墻腳邊打瞌睡。這是他的地盤,是他發見,而且曾經流了血來確定了他的所有權的。提到他這發見,倒也有一段小小的歷史,那是很久的事了,他第一次看見這漂亮的公共毛廁就覺得詫異:這小小的蓋造得頗講究的房子到底是“人家”呢,還是“公司”?那時正有一位大肚子穿黑長衫的走了進去,接著又是一位腰眼里掛著手槍的巡捕,接著又是一位洋裝先生,——嘿,都是闊人,都是隨時有權力在他身上踢一腳的闊人,他就不敢走近去。他斷定這小屋子至少也是“寫字間”了,不免肅然起敬。然而忽然他又看見從另一門里走出一個女人來,卻不像闊人們的女人。接著又有一個和他差不多的孩子也進去了,這可使得他大大不平,而且也膽壯起來了,他偷偷地踅近些一看,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那些闊人們進去辦的是那么一樁“公”事!他覺得被欺騙了,被冤枉地嚇一下了,他便要報仇;他首先是想進去也撒他媽的一泡尿,然而驀地又見新進去一人把一個銅子給了門口的老婆子,他又立即猜想到中間一定還有“過門”,不可冒昧,便改變方針,只朝那小屋子重重吐一口唾沫,同時揀定門邊不遠的墻腳蹲了下去,算是給這駭了他的小屋子一種侮辱。 那時,他并沒有把這公共毛廁的墻腳作為他的地盤的意思。然而先前進去的和他差不多的那個孩子這當兒出來了,忽然也蹲到他身邊,也像他那樣背靠著墻,伸長兩條腿,擺成一個“八”字。他又大大的不平。 “嗨!哪里來的小烏龜!”他自言自語的罵起來。 “罵誰?小癟三!”那一個也不肯示弱。 于是就扭打起來了。本來兩方是勢均力敵的,但不知怎地,他的腦袋撞在墻壁上,見了紅,那一個覺得已經闖禍,而且也許覺得已經勝利,便一溜煙逃走。只留下我們的主角,從此就成為這公共毛廁墻腳的占有人。 現在呢,他對于這公共毛廁的“知識”,早已“畢業”了;他和那“管門”的老婆子也居然好像有點“交情”。現在,當這不冷不熱又沒太陽又不下雨刮風的好日子,他蹲在他的地盤上,打著瞌睡,似乎很滿意。 這當兒,公共毛廁也不是“鬧汛”,那老婆子扭動著她的扁嘴,似乎在咀嚼什么東西。她忽然咀嚼出說話來了,是對墻腳地盤的“領主”: “喂,喂,大鼻子!你來代我管一管,我一會兒就回來的。” 什么?大鼻子!誰是大鼻子?打瞌睡的他抬起頭來朝四面看一下,想不到是喚他自己,然而那老婆子又叫過來了: “代我管一管罷,大鼻子;我一會兒就回來。謝謝你!” 他明白“大鼻子”就是他了,就老大不高興。他的爸爸媽媽還在的時候,他有過一個極體面的名字,他自己也叫得出來;可是自從做了街頭流浪兒以后,他就沒有一定的名字。最初,他也曾把爸媽叫他的名字告訴了要好的伙伴,不料伙伴們都說“不順口”,還是瞎七瞎八亂叫一陣,后來他就連自己也忘記了他的本名。然而,伙伴們卻從沒叫過他“大鼻子”。他的鼻子也許比別人的大一些,可是并沒大到惹人注意。他和他的伙伴對于名字是有一種“信條”的:凡是自己身體上的特點被人取作名字,他們便覺得是侮辱。例如他們中間有一個叫做小毛的癩痢孩子,他們有時和他過不去,便叫他“癩痢”。 因此,他忽然聽得那老婆子叫他“大鼻子”,他就老大不高興,然而不高興中間又有點高興,因為從來沒有誰把他當一個人托付他什么事情。 “代你管管么?好!可是你得趕快回來呢!我也還有事情。” 他一邊說,一邊就裝出“忙人”的樣子來,伸個懶腰站起了身子。 老太婆把一疊草紙交給他,就走了。但是走不了幾步,又回頭來叫道: “廿五張草紙,廿五張,大鼻子!” “嘿嘿,那我倒要數一數。” 他頭也不抬地回答,一邊當真就數那一疊草紙。 過不了十分鐘,他就覺得厭倦了。往常他毫無目的毫不“負責”地站在一個街角或蹲在什么路旁,不但是十分鐘就是半點鐘他也不會厭倦,可是現在他卻在心里想道: “他媽的,老太婆害人!帶住了我的腳了!走他媽的!” 他感到負責任的不自由,正想站起來走,忽然有人進來了,噗的一聲,丟下一個銅子。 從手里遞出一張草紙去的時候,“大鼻子”就感到一種新鮮的趣味。他居然“做買賣”了,而且頗像有點威權;沒有他的一張草紙,誰也不能進去辦他的“公”事。 他很正經地把那個銅子擺在那一疊草紙旁邊,又很正經地將草紙弄整齊起來。 似乎公共毛廁也有一定的時間是“鬧市”,而現在呢,正是適當其時了。各色人等連串地進來,銅子噗噗地接連丟在那放草紙的紙匣里,頃刻之間就有五六枚之多。這位代理人倒有點手忙腳亂了。一則,“做買賣”他到底還是生手;二則,他從來不曾保有過那么多的銅子。 他乘空兒把銅子疊起來。疊到第四個時,他望了望已經疊好的三個,又將手里的一個掂掂分量,似乎很不忍和它分手。可是他到底疊在那第三個上面,接著又疊上第五第六個去。 還是有人接連著進來。終于銅子數目增加到十二。這是最高的紀錄了。以后,這位代理人便又清閑了。 十二個銅子呢!寸把高的一個銅柱子。像捉得了老鼠的貓兒似的,不住手地搬弄這根銅柱子,他掐斷了一半,托在手掌里輕輕掂了幾下,又還過一個去,然后那手——自然連銅子!——便往他的破短衫的口袋邊靠近起來了。然而,驀地他又——像貓兒噙住了老鼠的半個身子卻又吐了出來似的,把手里的銅子疊在紙匣里的銅子上面,依然成為寸把高的銅柱子。 第二次再把銅柱掐斷,卻不托在手掌里掂幾掂了,只是簡潔老練地移近他的破口袋去。手在口袋邊,可又停住了,他的眼光卻射住了紙匣里的幾個銅子;如果不是那老太婆正在這當口回來,說不定他還要吐出來一次。 “啊,老太婆,回來了么?” 他稍稍帶點意外的驚異說,同時他那捏著銅子的手便漸漸插進了衣袋里。 老太婆走得上氣不接下氣似的,只把扁嘴扭了幾扭,她的眼光已經落在那一疊減少了的草紙以及壓在草紙上面的銅子。 “你看!管得好不好?明天你總得謝謝我呢!” 他說著,睒了一下眼睛,站起來就走。 走了幾步,他又回頭來看時,那老婆子數過了銅子,正在數草紙。于是他便想到趕快溜,卻又覺得不必溜。他高聲叫道: “老太婆!風吹了幾張草紙到尿坑里去了!你去拾了來曬干,還好用的!” 老婆子也終于核算出銅子數目和草紙減少的數目不對,她很費力地扭動著扁嘴說道: “不老實,大鼻子!” “怪得我?風吹了去的!” 他生氣似的回答,轉身便跑。然而跑得不多幾步又轉身擎起一個拳頭來叫道: “老太婆!猜一猜,什么東西?猜著了就是你的。哈哈哈!” 他一邊笑,一邊就飛快地跑過了一條馬路。 我們這位主角終于由跑步變為慢步了,手在衣袋里數弄著那些銅子。 一共是五枚。同時手里有五個銅子,在他確是第一次。他覺得這是一筆不小的財產了,可以派許多正用。他走得更慢了,肚子里在盤算:“弄點什么來修修肚臟廟罷?”然而他又想買一顆糖來嘗嘗滋味。對于裝飽肚子這一問題,他和他的伙伴們是另有一番見解的;大凡可以用討乞或者比討乞強硬的手段(例如在冷巷里攔住了一副吃過的飯擔子)弄得到的東西,就不應該花錢去買;花錢去買的,就是傻子! 至于糖呢,可就不同了。向人家討一粒糖,準得吃一記耳光,而且空飯擔里也決不會有一粒糖的。現在我們的主角手里有了五個銅子,就轉念到糖一類的東西上了。特別是因為他一次吃過半粒糖,所以糖的引誘力非常大。 他終于站住了。在一個不大干凈的弄堂口,有三四個小孩子(其中也有比他高明不了多少的)圍住一個攤子。這卻不是賣糖,而是出租“小書”(連環圖畫故事)的“街頭圖書館”。 對于這一類的“小書”,我們的主角也早已有過非分之想的。他曾經躲在人家的背后偷偷地張過幾眼,然而往往總是他正看得有點懂了,人家就嗤的一聲翻了過去。這回他可要自己租幾本來享受個滿足了。 “一個銅子租二十本罷?當場看過還你。” 他裝出極老練的樣子來,對那擺攤子的人說。 那位“街頭圖書館館長”朝他睄了一眼,就輕聲喝道: “小癟三!走你的!” “什么!開口罵人!我有銅子,你看!” 他將手掌攤開來,果然有五個銅子,汗漬得亮晶晶。 書攤子的人伸手就想抓過那五個銅子去,一面說: “一個銅子看五本,五個銅子,便宜些,看三十本。” “不成不成!十五本!喂,十五本還不肯?” 他將銅子放回衣袋去,一面忙著偷看別人手里的“小書”。 成交的數目是十本。他只付了兩個銅子,揀了二十本,都是道士放飛劍,有使刀的女人的。 他不認識“小書”上面的字,但是他會照了自己的意思去解釋“小書”里的圖畫。那些圖畫本來是“連環故事”,然而因為畫手不大高明,他又不認識字,所以前后兩幅畫的故事他往往接不起筍來。 可是他還是耐心的看下去。 有一幅畫是幾個兇相的男子(中間也有道士)圍住了一個女子和一個小孩子打架。半空中還有一把飛劍向那女的和那孩子刺去。飛劍之類,他本來佩服得很,然而這里的飛劍卻使他起了惡感。 “媽的!打落水狗,不算好漢!” 他輕聲罵著,就翻過一頁。這新一頁上仍舊是那女人和孩子,可是已經打敗了,正要逃到一個樹林里去,另外那幾個兇相的男子和半空中那把飛劍在后追趕。他有點替那女人和孩子著急。趕快再看第二頁。還好,那女人在樹林邊反身抵抗那些“追兵”了。然而此時圖畫里又加添出一個和尚,也拿著刀,正從遠處跑來,似乎要加入“戰團”。 “和尚來幫誰呢?”他心焦地想著,就再翻過一頁。他覺得那和尚如果是好和尚一定要幫那女人和小孩子,他要是自己在場一定也幫女人和小孩子的。然而翻過來的一頁雖然仍舊畫著那一班人,卻已經不打架了,他們站在那里像是說話,和尚也在內。 如果他識字,他一定可以知道那班人講些什么,并且也可以知道那和尚到底幫誰,因為和尚的嘴里明明噴出兩道線,而且線里寫著一些字,——這是和尚在說話。 他悶悶地再看下面一幅畫,可是仍舊看不出道理來。打架確是告一結束了,這回是輪到那女人嘴里噴出兩道線,而且線里也有字。 再下一幅圖仍有那女人和孩子,其余的一些人(兇相的男子們,道士,連和尚),都已經不見;并且也不是在樹林邊,而是在房子里了,女人手里也沒有刀,她坐在床前,低著頭,似乎很疲倦,又似乎在想心事;孩子站在她跟前,孩子的嘴里也噴出兩道線,線里照例有一些可恨的方塊字。 這可叫他摸不著頭腦了。他不滿意那畫圖的人:“要緊關口,他就畫不出來,只弄些字眼來搪塞。”他又覺得那女人和孩子未免不中用,怎么就躲到家里去了。然而他又慶幸那女人和孩子終于能夠平安回到了家——他猜想他們本來就是要回家去。 總而言之,對于這“來歷不明”的女人和孩子,他很關心,他斷定他們一定是好人。他熱心地要知道他們后來怎樣,他單揀那些畫著這女人和這孩子的畫兒仔細看。有時他們又在和別人打架了,他就由著自己的意思解釋起來,并且和前面的故事連串起來。不多一會兒,二十本“小書”已經翻完。 “喂,拿回去,二十本!還有么,講女人和孩子的?” 他朝那書攤子的人說,同時捫著自己的肚子;這肚子現在輕輕地在叫了。 書攤子的人一面招呼著另一個“小讀者”,一面隨手取了一套封面上畫著個女人的“小書”給了我們的主角。 然而這個“女人”不是先前那個“女人”了,從她的裝束上就看得出來。她不拿刀,也不使槍,可是她在書里好像“勢頭”大得很,到處擺架子。 我們的主角匆匆翻了一遍,老大不高興;驀地他又想起這一套新的“小書”還沒付租錢,便趕快疊齊了還給那書攤子的人,很大方的說一聲“不好看”,就打算走了。“錢呢?”書攤子的人說,查點著那一套書的數目。“也算你兩個銅子罷!” “什么,看看貨色對不對,也要錢么?” “你沒有先說是看樣子,你沒有罷?看樣子,只好看一本,你剛才是看了一套呢!不要多賴,兩個銅子!” “誰賴你的!誰……”我們的主角有點窘了,卻越想越舍不得兩個銅子。“那么,掛在賬上,明天——” “知道你是哪里來的雜種;不掛賬。” “連我也不認識么?我是大鼻子。你去問那邊管公坑的老太婆,她也曉得!” 一邊說,一邊就跑,我們的主角在這種事情上往往有他的特別方法的。 他保全了兩個銅子,然而他也承認了自己是“大鼻子”了。他覺得就叫做“大鼻子”也不壞,因為在他和他的伙伴中間,“鼻子”,也算身體上名貴的部分,他們要表示自己是一條“好漢”的時候總指自己的“鼻子”,可不是? 我們的主角,——不,既然他自己也愿意,我們就稱他為“大鼻子”罷,也還有些更出色的事業。 照例是無從查考出何年何月何日,總之是離開上面講過的“奇遇”很久了,也許已經隔開一個年頭,而且是一個忽而下雨忽而出太陽的悶熱天。 是大家正要吃午飯的時候,馬路上人很多。我們的“大鼻子”站在一個很妥當的地點,貓一樣的窺伺著“幸福的”人們,想要趁便也沾點“幸福”。 他忽然輕輕一跳,就跟在一對漂亮的青年男女的背后,用了低弱的聲音求告道:“好小姐,好少爺,給一個銅子。”憑經驗,他知道只要有耐心跟得時候多了,往往可以有所得的。他又知道,在這種場合,如果那女的撅起嘴唇似嗔非嗔的說一句“討厭,小癟三”,那男的就會摸出一個銅子或者竟是兩個,來買得耳根的清靜,——也就是買得那女人的高興。 可是這一次跟走了好遠一段路,卻還不見效果。這一男一女手臂挽著手臂,一路走著,自顧咬耳朵說話。 他們又轉彎了。那馬路的轉角上有一個巡捕。大鼻子只好站住了,讓那一對兒去了一大段,這才他自己不慌不忙在巡捕面前踱過。 過了這一道關口,他趕快尋覓他的目的物,不幸得很,相離已經太遠,他未必追得上。然而也還不至于失望,因為這一對兒遠遠站在那里不動了。 大鼻子立刻用了跑步。他也看清了另外有一個女人正在和那一對兒講話。忽然兩個女的爭執起來,扭打起來了,那男的急得團團轉,夾在中間,勸勸這個,又勸勸那個。大鼻子跑到了他們近旁時,已經有好幾個閑人圍住了他們亂出主意了。忽然有一個小小的紙袋(那是講究的店鋪子裝著十來個銅子做找頭的),落在地下了,只有大鼻子看到。他立刻“當仁不讓”地拾了起來,很堅決地往口袋里一放,就從人層的大腿間鉆出去,吹著口笛走到對面的馬路上。 逢到這樣的機會,大鼻子常常是勇敢的。他就差的還沒學會怎樣到人家口袋里去挖。 逢到這樣的機會,他又是十分堅決的,如果從前他“揩油”了管公共毛廁的那個老婆子的五個銅子,——這一項“奇遇”的當時,他頗顯得優柔寡斷,那亦不是因為那時還“幼稚”,而是因為他不肯不顧信用:人家當他朋友似的托付他的,他到不好意思全盤沒收。 天氣暖和時,大鼻子很可以到處為“家”。像他這樣的人很有點古怪:白天,我們在馬路上幾乎時時會碰見他,但晚上他睡在什么地方,我們卻難得看見。不過他到晚上一定還是在這“大上海”的地面,而不會飛上天去,那是可以斷言的。 也許他會像老鼠一樣有個“地下”的“家”罷?作者未曾調查過,相應作為懸案。 然而作者可以負責聲明:大鼻子的許多無定的“家”之一,卻是既不在天上又不在地下的。 想來讀者也都知道,在“大上海”的北區,“華”“洋”“交界”之地帶,曾經受過“一二八”炮火之洗禮的一片瓦礫場,這幾年來依然滿眼雜草,不失紀念。這可敬的“大上海”的衄疤上,有幾堵危墻依然高聳著,好像永遠不會塌。墻近邊有從前“繁華”時代的一口水泥垃圾箱,現在被斷磚碎瓦和泥土遮蓋了,遠看去只像一個土堆。不知怎的,也不知是何年何月,我們的大鼻子發見了這奇特的“地室”,而且立刻很中意,而且大概也頗費了點勞力罷,居然把它清理好,作為他的“冬宮”了。 這,大概不是無稽之談,因為有人確實看見他從這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下的“家”很大方的爬了出來。 這一天不是熱天,照日歷上算,恰是一年的第一個月將到盡頭,然而這一天又不怎樣冷。 這一天沒有太陽。對了,沒有太陽。老天從清晨起,就擺出一副哭喪臉。 這一頭,在“大上海”的什么角落里,一定有些體面人溫良地坐著,起立,“靜默三分鐘”。于是上衙門的上衙門,到“寫字間”的到“寫字間”……然而這一天,在“大上海”縱貫南北的一條脈管(馬路)上,卻奔流著一股各色人等的怒潮,用震動大地的吶喊,回答四年前的炮聲。 我們的大鼻子那時正從他的“家”出來往南走,打算找到一頓早飯。 他迎頭趕上了這雄壯的人流,以為這是什么“大出喪”呢。“媽的!小五子不夠朋友!有人家大出喪,也不來招呼我一聲么!”大鼻子這樣想著,覺得錯過了一個得“外快”的機會。他站在路邊,想看看那“不夠朋友”的小五子是不是在內掮什么“挽聯”或是花圈之類。 沒有“開路神”,也不見什么“頂馬”。走在前頭的,是長衫先生,洋裝先生,旗袍大衣的小姐,旗袍不穿大衣的小姐,長衣的像學生,短衣的像工人,像學徒,——這樣一群人,手里大都有小旗。 這樣的隊伍浩浩蕩蕩前來,看不見它的尾巴。不,它的尾巴在時時加長起來,它沿路吸收了無數人進去,長衣的和短衣的,男的和女的,老的和小的。 有些人(也有騎腳踏車的),在隊伍旁邊,手里拿著許多紙分給路邊的看客,也和看客們說些話語。忽然,震天動地的一聲喊——“中華民族解放萬萬歲!” 這是千萬條喉嚨里喊出來的!這是千萬條喉嚨合成一條大喉嚨喊出來的!大鼻子不懂這喊的是一句什么話,但他卻懂得這隊伍確不是什么“大出喪”了。他感得有點失望,但也覺得有趣。這當兒,有個人把一張紙放在他手里,并且說: “小朋友!一同去!加入愛國示威運動!” 大鼻子不懂得要他去干么,——這里沒有“挽聯”可掮,也沒有“花圈”可背,然而大鼻子在人多熱鬧的場所總是很勇敢很堅決的,他就跟著走。 隊伍仍在向前進。大鼻子的前面有三個青年,男的和女的;他們一路說些大鼻子聽不懂的話,中間似乎還有幾個洋字。大鼻子向來討厭說洋話的,因為全說洋話的高鼻子固然打過他,只夾著幾個洋字的低鼻子也打過他,而且比高鼻子打得重些。這時有一片冷風像鉆子一般刺來,大鼻子就覺得他那其實不怎么大的鼻子里酸酸的有些東西要出來了。他隨手一把撈起,就偷偷地撩在一個說洋話的青年身上。誰也沒有看見。大鼻子感到了勝利。 似乎鼻涕也有靈性的。它看見初出茅廬的老哥建了功,就爭著要露臉了。大鼻子把手掌掩在鼻孔上,打算多儲蓄一些,這當兒,隊伍的頭陣似乎碰著了阻礙,騷亂的聲浪從前面傳下來,人們都站住了,但并不安靜,大鼻子的左右前后盡是憤怒的呼聲。大鼻子什么都不理,只伸開了手掌又這么一撩,不歪不斜,許多鼻涕都爬在一個女郎的蓬松的頭發上了,那女郎大概也覺得頭上多一點東西,但只把頭一縮,便又脹破了喉嚨似的朝前面喊道: “沖上去!打漢奸!打賣國賊!” 大鼻子知道這是要打架了,但是他睒著眼得意地望著那些鼻涕像冰絲似的從女郎的頭發上掛下來,巍顫顫地發抖,他覺得很有趣。 隊伍又在蠕動了。從前面傳來的雄壯的喊聲像晴天霹靂似的落到后面人們的頭上——“打倒一切漢奸!” “一二八精神萬歲!” “打倒×——” 斷了!前面又發生了擾動。但是后面卻拾起這斷了的一句,加倍雄壯地喊道: “打倒××帝國主義!” 大鼻子跟著學了一句。可是同時,他忽然發見他身邊有一個學生,披一件大衣,沒有扣好,大衣襟飄飄地,大衣袋口子露出一個錢袋的提手。根據新學會的本領,大鼻子認定這學生的手袋分明在向他招手。他嘴里哼著“打倒——他媽的!”身子便往那學生這邊靠近去。 但是正當大鼻子認為時機已到的一剎那,幾個兇神似的巡捕從旁邊沖來,不問情由便奪隊伍里人們的小旗,又喝道: “不準喊口號!不準!” 大鼻子心虛,趕快從一個高個兒的腿縫間鉆到前面去。可是也明明看見那個穿大衣的學生和那頭發上頂著鼻涕的女郎同巡捕扭打起來了,——他們不肯放棄他們的旗子! 許多人幫著學生和那女子。騎腳踏車的人叮令令急馳向前面去。前面的人也回身來援救。這里立刻是一個爭斗的旋渦。 喊“打”的聲音從人圈中起來,大鼻子也跟著喊。對于眼前的事,大鼻子是懂得明明白白的。他腦筋里立刻排出一個公式來:“他自己常常被巡捕打,現在那學生和那女郎也被打;他自己是好人,所以那二個也是好人;好人要幫好人!” 誰的一面旗子落在地下了,大鼻子立刻拾在手中,拚命舞動。 這時,紛亂也已過去,隊伍仍向前進。那學生和那女郎到底放棄了一面旗子,他們和大鼻子又走在一起。大鼻子把自己的旗子送給那學生道: “不怕!還有一面呢!算是你的!” 學生很和善地笑了。他朝旁邊一個也是學生模樣的人說了一句話,而是大鼻子聽不懂的。大鼻子覺得不大高興,可是他忽然想起了似的問道: “你們到哪里去?” “到廟行去!” “去干么?這旗子可是干么的?” “哦!小朋友!”那頭發上有大鼻子的鼻涕的女郎接口說。“你記得么,四年前,上海打仗,大炮,飛機,××飛機,炸彈,燒了許多許多房子。” “我記得的!”大鼻子回答,一只眼偷偷地望著那女郎的頭發上的鼻涕。 “記得就好了!要不要報仇?” 這是大鼻子懂得的。他做一個鬼臉表示他“要”,然而他的眼光又碰著了那女郎頭發上的鼻涕,他覺得怪不好意思,趕快轉過臉去。 “中華民族解放萬萬歲!” 這喊聲又震天動地來了。大鼻子趕快不大正確地跟著學一句,又偷眼看一下那女郎頭發上的鼻涕,心里盼望立刻有一陣大風把這一抹鼻涕吹得干干凈凈。 “打倒××帝國主義!” “一二八精神萬歲!” 怒潮似的,從大鼻子前后左右掀起了這么兩句。頭上四個字是大鼻子有點懂的,他脹大了嗓子似的就喊這四個字。他身邊那個穿大衣的學生一面喊一邊舞動著兩臂。那錢袋從衣袋里跳了出來。只有大鼻子是看見的。他敏捷地拾了起來,在手里掂了一掂,這時——“打倒一切漢奸!” “到廟行去!” 大鼻子的熟練的手指輕輕一轉,將那錢袋送回了原處。他忽然覺得精神百倍,也舞動著臂膊喊道: “打倒——他媽的!到廟行去!” 他并不知道廟行是什么地方,是什么東西,然而他相信那學生和那女郎不會騙他,而且他應該去!他恍惚認定到那邊去一定有好處!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www.lz13.cn)!” 這時隊伍正走過了大鼻子那個“家”所在的瓦礫場了。隊伍像通了電似的,像一個人似的,又一句: “中華民族解放萬萬歲!” 1936年5月27日。 茅盾作品_茅盾散文 茅盾:嚴霜下的夢 茅盾:報施分頁:123
三十五歲之后 文/和菜頭 三十五歲是條界限,沒到界的還是三十露頭的年輕人,過了界的則屬奔四的中年人。 事情不是這樣的:你獲得了經驗,擁有了頭銜,甚至都有幾分睿智了,可以輕松一點過活,游刃有余地行走在社會里,開始感受成熟帶來的福利。真的不是這樣,三十五歲之后的感受更像是結束了適應性訓練,生活要給你來點真格的。 它的重量在短短幾年里翻著跟頭往上漲,世界也并沒有安寧下來,而是日甚一日的瘋狂旋轉。除了繼續挺下去,似乎你也沒有別的選擇。只是在這重壓之下,難免會隱隱有些擔憂,覺得自己會在某一刻終究承受不住,就那么一下子倒下來。 二十多歲的時候,感覺是自己張開雙臂迎上世界。三十多歲的時候,情況則是整個世界向你傾倒過來,聽得見自己身上骨節噼啪做響,一口氣屏住不敢有絲毫松懈。壓力來自四面八方,卻不再耗費你的體力,甚至無需動用你的智力,它只是簡單地耗神,好叫白頭發順著兩鬢瘋長。 我覺得在這個人生階段應該持有一種坦誠的態度,正如此刻去接受生命變化帶來的這一系列重量。如果自己已經被生活之錘反復鍛造成一塊通紅的銅,那么就應該像塊銅的樣子。不要解釋為自己內心火熱,也不應承諾自己還將堅固。靠堅固和鋒利可以走到今天,但我猜想接下去需要的只會是堅韌。 怎么理解這種變化呢?當自己還是個愣頭青的時候,世界由門組成。緩緩推開也好,飛腿踹開也罷,那時是暴力破解的年月。世界有無限多扇門,你可以打開無限多種可能。但是探索到一定的時間,你終將明白一點:一生不可能全然在不斷開門里度過。一定有某扇門,或者某幾扇門,打開之后自己可以走進更深遠的世界。 把自己托付給智慧也好,純粹的欲望也罷,你會一路這么走下去,那是屬于你的一部分。你可以為之努力,在自己的沙漏清空之前走到你認定的處所。并且,因此不再羨慕別人選擇的門,和別人走過的路。知道自己能力所能達成的極限,這是狂心消歇的開始,但是并不會讓人感覺到多少快樂。 因為許多東西會因此崩壞掉。有些你曾經認定是堅固的,甚至是美好的東西,很快會因此而破碎。當你仔細地領悟到人人時間都有限這一點后,就會很快看明白大家都在舞台上為了什么而急切。許多漂亮的大詞都會因此而支撐不住,許多漂亮的人物也都會因此而原形畢露,你看見其實只有生存法則在起著作用,無非是在它驅動下的行為中有些更具迷惑性,而另外一些容易圖窮匕見。 凡事問一句:他/它指著什么吃呢?“以何為生”是把銳利的刀子,用來做現象和實質的切割再合適不過。一地零碎之后,會發現可以稱之為真正問題的不多,可以稱之為純粹觀念的東西也不多。往昔自己曾追逐的熱鬧就像萬花筒,炫目的幻相之下只有三棱鏡面和一些碎紙屑而已,它們對現實無能為力。 我個人的現實又是什么? 我有了間書房,書架上放了三盆綠色植物。因為煙熏的緣故,它們都羸弱不堪,葉子總是無法垂下來,按照當初設計的那樣遮住書架的最上一層。書桌上是一台筆記本電腦,邊上總是摞著幾本書。看完一本就撤掉一本,有新書來就繼續碼上去。在書和電腦之間,則是無數的轉接線、連接線、充電器以及各種小型電子產品。 中間有一只藍色的塑料盒子分外醒目,里面是一個塑膠的半透明牙套,叫做“止鼾器”,據說可以防止呼吸暫停。沒有人會在二十幾歲的時候擔憂呼吸暫停癥,但是在我這個年歲,就得開始像個拳擊手一樣咬著牙套,連睡夢都變成了致命的拳台。以前總希望自己能在人生路上“武裝到了牙齒”,我卻不知道竟然是以這樣一種武裝方式。 書桌是既有之物的陳列,籠罩貪婪的光輝。止鼾器則是對于死亡的恐懼,那暗影已經漸漸逼近。35歲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的平均壽數,考慮到數百萬年的時光,這個數字可能還會更小一些。這也就是說,即便現代社會里的人能夠活到七、八十歲,但是有些恐懼已經寫進了DNA里。遠離了天花、肺結核,人到了這個均數的年齡之后,還是會無端端地覺得恐慌。加上所謂本命年的存在,如果你又恰好在事業上選擇了較為艱難的路線,那么總是會覺得心頭沉甸甸的,又不知道為了什么。 而與此同時,你的朋友熟人家里在添丁,自己的父母卻垂垂老去,生命的潮汐漲落帶來秋日的蕭瑟。人們這時去繁衍后代,與其說是賦予孩子生命,倒不如說是因為新生兒點亮自己的生命驅散開死亡的陰影。我看到朋友們情深入許,為孩子寫下深深淺淺的文字,其實也都是為了自己,給自己中年的生命一次重新賦值,似乎和更為遙遠的未來扯上了什么關系,自己因為責任而擁有了某種價值。 為別人活著或許是令人煩惱的,但是若無需如此,則需要更大的重量避免自己的靈魂隨風飛去。就這樣,少年人一路遠奔,此時卻漸漸回返原路。有的人說:我驚訝地發現自己變成了年輕時所厭惡的那一類人。也許吧,只不過那時候生命還沒有多少重量而已。 我已經覺察到很多變化,包括夜里額外多出的一次起夜,包括案頭常備的胃藥。以前會相信一切不適都是暫時的,一覺起來也許都會好起來。即便一時不是如此,也有信心認為會有那么一天。現在我不那么想了,我開始相信可能從此要帶著這些不適一路走下去。 這固然讓人覺得不那么愉快,但也只能作為生命的一部分接受下來,就像樹木帶著節疤繼續成長。繼續長下去,帶著所有不適的人物和事情。樹就站在那里,似乎除了這么繼續下去,也不會有什么別的選擇。在追尋一個美好的世界如此之久以后,試著和一個不那么完美的世界并存。當我再次看到這世界的黑暗創口時,想得更多的是自己身上對應著的瘡疤,想著我們彼此映射,想著自己不可能飛升到純粹的光明里去。 本命年里會有許多選擇,黃歷上卻寫著諸事不宜。帶著這樣的壓力、疲憊、創痛和恐懼,為什么還要走下去,又要走向哪里?(www.lz13.cn)幾天前和老友們喝酒聊天,我的一位老哥哥說到他生意上的事情。他說他費盡千辛萬苦,終于中標簽合同。可剛到工地的時候,就被甲方一個小他二十幾歲的姑娘惡罵凌辱。 他坦誠地說,在那一剎那,他很想計算一下這些年賺了多少錢,如果達到自己心里那根保底的線,他想立即退出,什么都不做了。也正是在那樣一閃念之間,他被自己的這種念頭所震驚,“我怎么會變成這種人了?” 老哥哥一下子就崩潰了,羞愧讓他淚流滿面。和壓力相比,更可怕的是自己背叛了自己。而困難之處在于,到了這樣的年歲,即便你這么做了,也沒有人能指責你什么。反而可能會贊揚你務實,懂得進退之道。 我倒寧可繼續活得虛無一些,看不清楚十年之后會是怎樣。始終留存有一夜之間一切不復存在的可能,這讓人能夠走得更快一點,更遠一些。就像我的老哥哥他們一樣,坦誠地面對自己的欲望,堅定地捍衛自己的審美,然后嚴厲地對待自己的怯懦。當初是自己選的這扇門,那就要一路走到底。我們是那樣的不完美,卻又是如此的堅韌。軟弱有時,脆弱有時,但總是要開出花來。 35歲以前,你應該盡可能做到的十件事 從30歲到35歲:為你的生命多積累一些厚度 成功八大資源:請在35歲前搞掂分頁:123
ACC711CEV55CE
台中南屯建設公司稅務諮詢
對方不給我扣繳我請不到人又用他不可,怎麼辦? 電池材料相關產業節稅方式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是什麼?費率多少?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